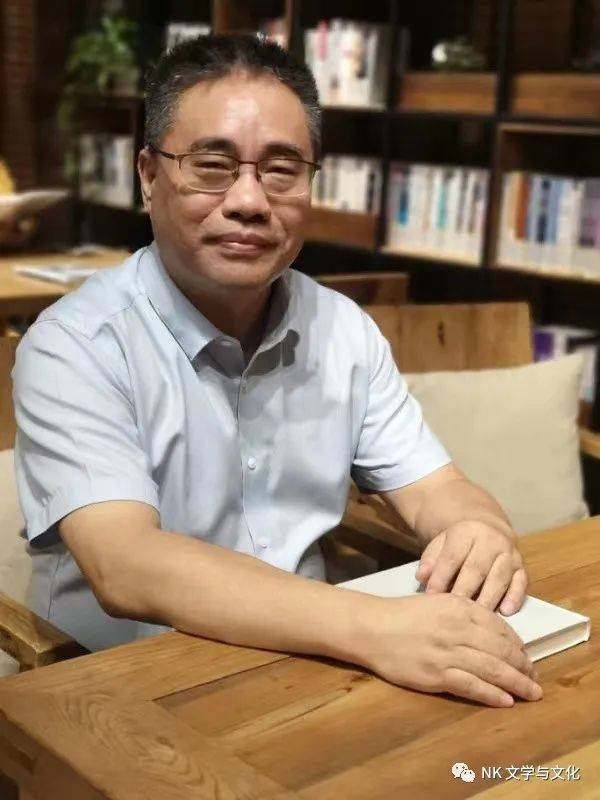
刘勇刚
内容提要:吟诵是一种依据文字的声调行腔使调的读书法,是介于诵读与唱歌之间的汉文古典作品口头表现艺术形式。吟诵自由、即兴,重在因声求气,涵咏入境,亲切地体会作品而没有乐谱的限制。吟诵的规律大抵有三条:平长仄短、平低仄高或平高仄低、平直仄曲。方言不同,文体相异,吟诵的调式亦各具形态。吟诵注重从声音证入,乃创作与鉴赏古典诗文的不二法门,又系国学教育、文学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吟诵源于我国诗乐一体的传统,吟诵声腔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来的佛经转读有关,主要得力于有清一代桐城派古文家的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渐趋式微。唐文治与赵元任是近现代吟诵的先驱。20世纪90年代以来,吟诵重振,渐呈中兴之象。吟诵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小众文化,品位高雅,在当下多元艺术门类中有其存在的空间。
关键词:读书法 因声求气 吟诵的特点与规律 吟诵的功能 小众文化
吟诵是古人口耳相传的读书法,堪称美读,是一门高雅的口头表现艺术。但是在现代朗诵与流行歌曲盛极一时的今天,吟诵几乎沦为绝响,抢救、采录、传承吟诵实属当务之急。原生态的吟诵本无乐谱,表现形式上自由、即兴,却自有其特点与规律,并非任情而发,信口而歌。吟诵是文学创作、鉴赏和传播的方式,又承载着国学经典,肩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吟诵之声即天地之元声,它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绝不能任其汩没而不能自振。重振吟诵既不宜走士大夫式的阳春白雪的路径,也不宜趋附流行文化,吟诵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下有其自身的定位和存在的空间。
一、吟诵的特点与规律
什么是吟诵呢?吟诵是一种依据文字的声调行腔使调的读书法,是介于诵读与唱歌之间的汉文古典作品口头表现艺术形式。从音乐的原理说,“吟”是用一个长音或是数个音连缀成的“拖腔”长言咏叹,节奏较舒缓;“诵”是用一二个短音急读,节奏较快,不拖腔。平声字多吟,仄声字多诵。“吟”与“诵”交错在一起,相间而行,宽紧相济,相反相成,是吟诵在音乐节奏方面总体上的情形。古人读书有吟有诵,或既诵且吟,“吟诵”二字连缀则出现于中古。如《晋书·儒林传·徐苗》:“苗少家贫,昼执锄耒,夜则吟诵。”[1]《隋书·薛道衡传》:“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2]古汉语多单音字,单音字有各自独立的意义。诵、歌、吟的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任二北先生《唐声诗》一书对此有精到的辨析:“惟‘诵’之声无定调,为朗读,为时言;歌之声有定调,为音曲,为永言。诵欲有所讽谏,故吐辞必近语言,以便当面晓悟;歌之用在感发,故衍声必符乐曲,以利远飏而激众。既不能指诵声为歌声,混诵诗为歌诗,即无从以‘诵诗’二字代“‘声诗’。”[3]又云:“诗与文之朗诵,在唐、宋均颇考究。善诵者可以发明诗文之精义,使人开悟,而得其余味;可以显示诗文中之结构、作用,使人得谋篇修辞之法。此种诵之音乐性比较最淡,固不如歌,且不如吟。”[4]照任先生看来,诵比较直白,声无定调,音乐性比较淡薄,感发的效果不如歌诗和吟诗。诵以声节之,注重语音的节奏,古今没有太多的变化,吟则介于念读与歌唱之间。吟是古人独有的,以音乐的节奏为主,因此吟诵本质上偏重在吟。赵元任先生说:“所谓吟诗吟文,就是俗话所谓叹诗叹文章,就是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而不用说话时或读单字时的语调。”[5]赵氏所说的“拉起嗓子来把字句都唱出来”只是对“吟诗吟文”的一个通俗的说法,并非严格地下定义。吟与唱歌不同,吟的弹性较大,行腔使调的长短高低曲直比较自由、即兴,而且没有和声效果。赵元任先生儿时受过旧式国学吟诵教育,后来长期研习西洋音乐,对吟与唱、诗与歌有非常知性的辨析:
中国的吟诵是大致根据字的声调来即兴的创一个曲调而不是严格的照着声调来产生出一个丝毫不变的曲调来。[6]不消说吟之所以为吟,跟唱歌的不同,就是每次不一定完全一样吟法。[7]诗是诗,歌是歌,诗歌愈进步,它们就免不了愈有分化的趋势;太坏的诗,固然不能作顶好的歌,可是好歌未必是很好的诗,顶好的诗也未必容易唱成好歌。……可见读诗有读诗的味儿,唱歌有唱歌的味儿,而且不是能够同时并尝的,诗唱成歌就得牺牲掉它的一部分的本味,这是不得不承认的。所以唱歌的兴趣完全是另一种兴趣。[8]
赵先生所说的“曲调”、“唱歌”是以西洋音乐的五线谱为参照系的,西洋音乐的谱曲可以不依字的声调,一旦谱成曲就是固定的,唱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谱子唱,不能有出入。其实,中国古典音乐的工尺也相当严,并不输给西洋音乐。元人燕南芝庵《唱论》就指出:“(唱歌)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字真,句笃,依腔,贴调。”“有字多声少,有声多字少,所谓一串骊珠也。”[9]而中国的吟诵大致依据字的声调行腔使调,音值不固定,有其灵活性。吟诵与唱歌自有其分野。诗并不一定都要唱成歌,就如同中国诗与中国画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好歌与好诗的标准也不一样,吟诵有吟诵的妙处,唱歌有唱歌的妙处,各得其本味,各得其美感,实无优劣高下之分。吟诵的规律大致有三条:平长仄短、平低仄高或平高仄低、平直仄曲。[10]平长仄短是汉语平声长仄声短的自然语音决定的,是吟诵最重要、最基本的规律。北语吟诵最重平声和去声。清人徐大椿《乐府传声》指出:“四声之中,平声最长,入声最短。盖平声之音,自缓、自舒、自周、自正、自和、自静,若上声必有挑起之象,去声必有转送之象,入声之派入三声,则各随所派成音。故唱平声,其尤重在出声之际,得舒缓周正和静之法,自与上去迥别,乃为平声之正音,则听者不论高低轻重,一聆而知其为平声之字矣。”[11]又云:“去声最有力,北音尚劲,去声真确,则曲声亦劲而有力,此最大关系也。”[12]至于南方方言(粤语、闽语、吴语、客语、湘语、赣语等)还保留着若干原生态的入声古音,吟诵时除了注意平声和去声,还得把入声字读出来。这一点下文有集中论述,这里暂不展开。平低仄高或平高仄低则关乎南方方言与北语(普通话)各自的声调系统,方言不同,音值亦不同。南方方言吟诵普遍采用平低仄高的调式,普通话吟诵则转用平高仄低。平直仄曲系吟诵旋律形态之规律,平直即平声字用平直的音去吟,仄曲即仄声字用变度音(曲折的音)去吟。此外,吟诵如唱法,还须讲究起调、断腔、顿挫、轻重、徐疾等。起调之紧要在首字之蓄势,首字一开,通首皆活;断腔在于声音的转折,续中有断则神情方显;顿挫与驰骤相反相成,其要诀在化声音为形象,臻于胜境则形神毕出,宛然如在目前;轻重则是吐字飘逸、沉着之谓;徐疾则在行腔节度之一贯,字句之分明。吟诵的调式有其多元性,这主要是方言和文体的差异性所致。方言不同,读音各异,自然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吟诵调式。同样的一首诗,用不同的方言去吟诵,会有不同的调式版本。总的来看,南方方言保留了古入声字,而普通话却没有入声字,吟诵的吐字与腔调就有较大差异。老一辈吟诵学家对入声字读法尤为着意,常州吟诵传人屠岸先生指出:
入声字在三个仄声(上声,去声,入声)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入声短促,急切,强烈,如乐手击鼓桴,雷公打霹雳。入声使诗文的吟诵如乐曲增添了节奏的强度,如绘画突出了闪电的亮色。在语音的变化发展进程中,今天的普通话里入声消失了:原入声字一部分变成了平声,一部分变成了上声和去声。用普通话朗诵(不是吟诵)古诗文,没有入声,这对我的听觉来说,是一种缺失。用常州音吟诵古诗文,保留了入声,它像出土文物,应当倍加珍惜。入声由于具有突击式的节奏感,有的入声字即使韵母不同,也可用来押韵。……只有用保留入声字发音的吟诵调吟诵,才能体现出入声的这种微妙处。如果用没有入声的普通话朗诵,这种特殊的音韵美便不存在了。[13]
原汁原味的入声字“具有突击式的节奏感”,吐字斩截有力,有拗怒之音,能增加吟诵节奏的力度、强度和亮度,其微妙之处确乎在此。因此,南语吟诵时对入声字的处理宜遵照古音,遇入声读入声。但普通话吟诵遇到古音入声字吐不吐入声呢?这在吟诵学界有争议。我认为吟诵的调式是多元化的,亦不宜过分地强调入声字,普通话吟诵注意入声自然古意盎然,但入派三声也是一种路数,毕竟吟诵是活态的存在,应吸纳现代语音元素,无须泥古不化。有的吟诵学家认为,普通话吟诵不仅要考究入声字,叶音和破读亦不可等闲视之。吟诵学家张本义先生指出:
叶音是解决汉字由于古今音异,造成诗文韵脚不谐的一个行之有效地老办法。古今读音不同的字,若处在诗词韵文句子中间位置,不刻意处理也无大碍,甚至用今音吟诵也未尝不可。而在韵脚之处,则须依叶音例加以谐之。破读原本就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现象。……再说破读。它原本就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现象。文读(书房音)和白读(白话音)的分歧、方言差异、读写讹误和为适应诗词格律而采取的变读等,是造成破读的原因。这个现象,在古代诗文中普遍存在。[14]
持论颇中肯綮。叶音主要运用于韵脚以达到同声相应的效果,如“浑欲不胜簪”的“簪”字应读“zēn”,“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字应读“xiá”,但不宜扩大化。破读则是古汉语中的多音字现象,如“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雨”字应读去声,尤其是近体诗节奏点上的字更要采取破读的方式,如“却看妻子愁何在”、“遥看瀑布挂前川”的“看”字均应读成阴平,不可念去声,否则上下句的平仄就不叶了。诗词文文体相异,吟诵的调式与乐感各有不同。就诗而论,古体吟诵与近体吟诵的侧重点亦有差异。郭绍虞先生指出:“窃以为声律之论,古调律调确有分别。古调乃自然之音调,律调则人为的声律。所以古调以语言的气势为主,而律调则以文字的平仄为主。”[15]可谓要言不烦,得其壸奥。古调吟诵不雕不琢,讲究自然流转的气势,节奏音律颇有素朴之美。近体律调则依据文字的平仄来行腔使调。近体有律绝之分,又有平起与仄起的分别,吟诵的调式的规律好掌握一些,可以套吟,但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声情,宜深加吟味,不可千篇一律,机械雷同。词为曲子词,原初为配乐歌唱的乐府诗,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字分平仄,还要严辨上去,该用去声的不得以上声代之;句法长短参差,节奏、用韵较之诗更为繁复。词的吟诵还要讲究择调,以使情与声合拍。如《念奴娇》这个词牌的来历与唐代女高音歌唱家念奴有关,据唐人笔记记载“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16],因此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声情以铜琶铁板之音为当行本色。再如《满庭芳》以深情绵邈见长,秦观的“山抹微云”走红于词坛,与其声情之柔美大有关系。总体来看,词的吟诵难度较大,但甚为美听。文的吟诵自由度较大,音情顿挫,气盛言宜,最重拖腔,尤其是尾腔的处理要摇曳生姿。规律是从吟诵实践中抽绎出来的,其目的还在于深度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吟诵是即兴的、自由的,有其审美的张力。吟诵能溢出规律之外,打破工尺的铁律,所以五音繁汇,千姿百态。对此叶嘉莹先生发表过很好的意见:
中国的吟诗,一定不能谱成一个调子,一定不能有死板的音节,一定要有内心的体验和自由。为什么不能谱成一个调子呢?因为你每次读一首诗都可以有不同的感受,而且不同的人读这首诗感受也不同,吟诵的时候一定要把对这首作品的体会和情意用自己的声音表现出来。……因为诗歌的感情不同,仄声有时也可以拖长,甚至于入声,你把它收住以后,调子也一样可以拖长。中国的吟诵没有必然地说哪个字长,哪个字短,哪个字高,哪个字低。因为作者的背景不同,写作诗歌的感情也不同,它是变化万端,但节奏一定是一样的,在常态的规律之中有抑扬高低的变化。[17]
至于吟诵能不能谱成一个调子,谱成了一个调子是不是就一定造成死板的音节,这个问题事关吟诵的传承和具体实践,可以进一步商榷[18],但叶先生论吟诵将着眼点放在“内心的体验和自由”,堪称探骊得珠。进而论之,因为每一次吟诵的体验是有差异的,自然亦可打破平仄声调的限制,“在常态的规律之中有抑扬高低的变化”,比如笔者听过扬州前辈学人朱福烓先生江淮官话的吟诵[19],就几乎突破了平长仄短的规则,平亦长,仄亦长,甚至入声亦拖腔,而自有一番韵味。
二、 吟诵的功能
吟诵源于我国诗乐一体的传统。先秦的诗三百篇是诗与雅乐的结缘,汉魏六朝的乐府则是诗与清商乐的结合,隋唐以来的曲子词则是伴随燕乐的蕃盛而勃兴的,依次而演进,宋代的说唱文学、元明清的戏曲,无一不是诗乐的配合。有诗有乐,斯有吟诵。诗乐结合的历史即吟诵的生成历史。《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20]先秦时期,诗、歌名为二而实不可分,诗是吟,歌亦是吟,曼声咏唱,又以律吕调和之。此后,诗与乐逐渐分家,诗是诗,乐是乐,然“诗为乐心,声为乐体。”[21]诗依然不失声音的美听。迨至魏晋,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自觉的标志即体现在对文采和声音的重视。陆机《文赋》云:“诗缘情而绮靡。”[22]“绮”言其色彩,“靡”说的就是声音了,“绮靡”即辞藻华丽,声情并茂。南朝梁元帝《金楼子·立言》也有相似的表述:“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3]沈约是永明新体诗的开创者之一,受东晋南朝以来佛经转读的影响,倡四声八病之说,意谓平上去入各得其所,八病尽能规避,即可臻于“八音协畅”之境界。刘勰《文心雕龙》对诗乐之辨更有知性的分野,设《明诗篇》和《乐府篇》分别加以阐论,但又注意到诗与乐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神思篇》谓“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24],《物色篇》云“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25],都说的是为文的声音之道,亦即“声文”。《声律篇》则专门讨论诗歌的音律:“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26]在刘勰看来,缀文过程中声律的安排离不开“吟咏”——“声转于吻”。吟诵是对音节韵律的感性体验,在创作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韩愈《答李翊书》云:“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7]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则说:“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28]韩、柳所云均从声音之道论作文之要法,颇得其要领。写诗有妙手偶得的好运气,但真正的好诗,往往是长期苦吟出来的;历代多苦吟诗人,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苦吟所考虑的因素虽是多方面的,但无疑包含着音律的推敲。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29],卢延让也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30],“长吟”、“吟安”就是放出声音来,曼声吟哦,用心体会诗的韵律节奏。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论诗最重音律,堪称探本之论: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31]
诗乃乐教,诗与乐虽判为二而实为一,诗不徒为格律化的“排偶之文”,而应有乐声之和,音韵之美,这样才能“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至于说到“手舞足蹈”,实乃吟诵之境界。词的音乐性比诗要丰富得多,倚声填词更须歌诵。张炎《词源》说:“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32]真乃深得个中甘苦。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作者要把声音韵律的因素考虑进去,否则诗词文如腐木湿鼓,又有何意味呢?古人学诗从吟诵入手,这一点明清人总结得最为醒豁。谢榛《四溟诗话》指出:“凡作近体,诵要好,听要好,观要好,讲要好。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独茧抽丝。此诗家四关。使一关未过,则非佳句矣。”[33]又云:“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34]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也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35]“往复讽咏”亦即“熟读之,歌咏之,玩味之”,如此则渐入佳境。文学的玄妙之境,往往在“抑扬抗坠,密咏恬吟”之间,从容涵咏,酝酿日久,自能“造乎浑沦”,得文学之三昧。诗词乃吟咏情性,既讲四声阴阳,抑扬抗坠,那么读者审美鉴赏文学作品自然也应该从“吟咏”入手,披文以入情。王夫之说得好:“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36]古人读诗词文皆曼声长吟,品尝其音节之美,进而由音节之美体悟意境之美。所谓“因声以求气”,就是纵声朗吟或低声讽诵,这历来被视为鉴赏古典诗词的妙法。朱熹谈到《诗经》的欣赏时说:“此等语言自有个血脉流通处,但涵咏久之,自然见得条畅浃洽,不必多引外来道理言语,却壅滞却诗人活底意思也。”[37]严羽《沧浪诗话》论诗法,有音节一法,主张永言诵读:“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38]元人刘绩云:“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为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39]所谓“活底意思”、“金石宫商之声”都是讽诵涵咏出来的,“吟而绎之”就是一个吟诵玩味的过程。现代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亦对吟诵体会颇深,他在《精读指导举隅·前言》中指出:“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40]吟诵即“亲切地体会”,沉吟其中,不仅能提高古典文学鉴赏的水平,久而久之,“内容与理法”即能内化为自己的质素。欣赏诗的要务无非是营构一个美的意象世界,而吟诵对于诗歌委实是一种有意味的、合目的性的再创造活动,因为从诗的音声韵律中能生发出形象,品味出意境,领略出情趣。诗出于音乐,这注定诗歌与音乐声息相通,即使原初的乐调或工尺失传,不复可歌,但依然会“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的节奏音调”[41],所以“诗人不得不在文字本身上做音乐的功夫”[42]。吟诵作为具有音乐形态的口头表现艺术诚然有自娱娱人的价值,但深层次的意义绝不止于表演,而是本之情性,体之于心。《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云:“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43]音乐之声来源于人的心灵的感应,文采节奏看似无形而实乃有形,乃乐之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乐不可以为伪”[44]。钱锺书《管锥编》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乐论,指出:“声音为出于人心之至真,入于人心之至深,直捷而不迂,亲切而无介,是以言虽被‘心声’之目,而音不落言诠,更为由乎衷、发乎内、昭示本心之声……要知情发乎声与情见乎词之不可等同,毋以词害意可也。”[45]可称抉微之论。叶嘉莹先生论诗最重感发,而内心感发的唤起与吟诵有莫大的关系,她说:
我理解的吟诵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别人听,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心灵与作品中诗人的心灵能借着吟诵的声音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因此,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古典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特质,也是与吟诵之传统密切结合在一起的。[46]
进而论之,吟诵的声音要与古人的心灵相通,“达到一种更为深微密切的交流和感应”,就必须反复揣摩古人的文字,这样“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47]。吟诵是诗教、乐教,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旧式正统教育传播国学,吟诵堪称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亦是人才培养之大法。虽然就具体音乐形态而论,吟与诵各有偏重,但都具有节奏韵律之美。《周礼·春官》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48]。兴者,兴发感动;道者,引导也;讽者,不开读,即背诵;诵者,以声节之。“言”和“语”则是对答,也就是引诗,运用于外交场合的赋诗断章。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49]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的最终目的在于作育人才。音乐关乎性情之邪正,乐教的功能即陶冶人之性情,“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50]。清人徐大椿《乐府传声》一书认为“古人作乐,皆以人声为本”,将传声上升到“陶情养性之本”、“学问之大端”[51],足以昭示吟诵在内的乐教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价值。近代教育家唐文治更是本着《乐记》“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的精神对读文作了透辟的论述。如《国文大义》:
盖文章之道,所以盛者,实在于声,所以和声乃可鸣盛也。……作乐之蕴,要在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夫然后能安其位而不相夺。盖不散、不集、不怒、不慑者,乐律之本原,而亦文声之秘钥也。是故文之声贵实而戒浮,实则沉,浮则散。文之声贵疏而戒滞,疏则朗,滞则集。文之刚者其气宜直而勿暴,暴其气则声怒。文之柔者其气宜和而勿馁,馁其气则声慑。[52]
照唐先生看来,人的性情亦如天地之道无非是阴阳刚柔,但性情之养成离不开读文,读文乃教育精神之所在,读文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读文的过程也就是“品行文章,交修并进”,进而“成智成圣”,躬行实践的过程。唐文治崇尚精英教育,先后主政上海交通大学和无锡国学专修馆,常欲造就领袖人才,造就的方式则离不开读文,他在《学校论》中甚至强调“令各学校于读经之外,一律诵读国文,其不通国学者,概不得毕业”[53]。从当代的教育精神来看,一味强调尊孔读经,已经不合时宜,但诵读国文,通晓国学是任何时候都不过时的。
三、吟诵之盛衰与中兴
吟诵源远流长,正如上文叶嘉莹先生所说,“中国古典诗歌之生命,原是伴随着吟诵之传统而成长起来的”。吟诵之风与汉末以降的佛经转读有关。南朝梁时善声沙门慧皎指出:“转读之为懿,贵在声文两得。若唯声而不文,则道心无以得生;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故经言,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斯之谓也。”[54]转读最重四声,具有修饰之美,对永明声律影响甚大,声律最终落实到声音上,也就是“声文两得”——吟诵。但吟诵大得盛行于世乃得力于桐城派的倡导。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在于桐城。桐城派古文家论文特重音节,皆主张从声音证入,因声而求气。刘大櫆《论文偶记》云: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55]
神气是玄虚抽象的,但文章的音节、字句是具体的、感性的,吟诵时音节的抑扬抗坠能传达出作者心灵的律动,入情入境地吟诵古人文字,古人营构的意象世界便活脱脱地浮现在眼前。姚鼐论文亦根柢于音节,对古文的读法与风格有细致的探讨。他晚年在给弟子陈用光(字硕士)的信中说:“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文韵致好,但说到中间,忽有滞钝处,此乃是读古人文不熟。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56]质言之,“从声音证入”就是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奏抗声引唱,去体悟文章的韵致。姚鼐审美重阳刚阴柔。照他看来,阳刚与阴柔各有其造境,各有其声色之美。不仅要具眼(“观其文”),还得具耳(“讽其音”),落实到音节上,从声音证入以领悟美感的不同形态。曾国藩秉承姚鼐阴阳刚柔之说,付之于实践,编成《古文四象》一书传诵天下。所谓四象乃从阴阳衍生而来,参天地之消息。曾国藩对古文四象的分类是:太阳气势、太阴识度、少阳趣味、少阴情韵。四象就是文章的四种体性。曾氏的“四象说”立足于音节,即文章的神情意态最终要落实到声音上来,从声音的变化去感知四象之美。他强调古文要“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复,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57]。在具体的读法上,他主张:“先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朗朗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58]持论隐承姚鼐“急读缓读”之法而来。方东树论读法,则主张“沉潜反覆,讽玩之深且久”[59],讽玩的入口在于阴阳四声:“音响最要紧,调高则响。大约即在用字平仄阴阳上讲,须深明双声叠韵喜忌,以求沈约四声之说。同一仄声,而用入声,用上、去声,音响全别,今人都不讲矣。”[60]梅曾亮与吴汝纶论吟诵偏重于“气”。梅曾亮《与孙芝房书》指出:“夫观文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61]一个“气”字听起来玄妙,其实不外乎人之胸襟气度学养,是为“至精”。一旦“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我与古人的性灵便臻于浑然无间之境界。吴汝纶系曾门弟子,秉承师说,对吟文之法更有发挥。他说:“读文之法,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气,不听之以气,而听之以神。大抵盘空处如雷霆之旋太虚,顿挫处如钟磬之扬余韵。精神团结处则高以侈,叙事繁密处则抑以敛;而其要者纯如绎如,其音翱翔于虚无之表,则言外之意无不传。”[62]照他看来,古人之大文皆昌于气,此气流于唇吻,通于乐理。张裕钊在总结桐城派声音之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因声以求气”的理论命题,他在《答吴挚甫书》中说:
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欣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63]
文章的法度是抽象的,而音节是感性的、流动的,音节的摇曳变化,通于灵府,“因声以求气”,“讽诵之深且久”,即能“通乎其微”,深契古人精深华妙之境界。
桐城派吟诵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是前面提到的唐文治。唐文治在曾国藩《古文四象》的基础上将古文读法分为五种:急读、缓读、极急读、极缓读、平读,各有其声情:“大抵气势文急读极急读,而其音高;识度文缓读极缓读,而其音低;趣味情韵文平读,而其音平。然情韵文亦有愈唱愈高者,未可拘泥。”[64]他认为文章之妙在“神、气、情”三字,将吟文总结成十六字诀:“气生于情,情宣于气,气合于神,神传于情。”[65]可谓集吟文之大成。他的古文吟诵韵味十足,独树一帜,被称为“唐调”,风靡一时。
在桐城派的倡导下,吟诵在学界颇为盛行,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桐城派被视为“谬种”,传统吟诵亦被当作糟粕遭到了废弃。大学国文教育不再有吟诵弦歌之声,有识之士深为之扼腕。朱自清曾不无惋惜地说过这样的话: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学校里废了吟这么多年,即使是大学高才生,有了这样成见,也不足怪的。但这也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66]
现在教师范读文言和旧诗词,都不好意思打起调子,以为那是老古董的玩意儿。其实这是错的,文言文和旧诗词等,一部分的生命便在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知道它们的味儿。[67]
朱自清当年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一线教师,又系古典文学专家,他说废弃吟诵是“教学上一个大损失”,确属剀切之言。不过,朱先生说“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我不以为然。其实“摇头摆尾”也就是《毛诗序》讲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8],正是吟诵入境的状态,乃“情之所至,气之所激,意之所专”[69],是一种自然的体态律动,而非刻意的作秀。谈到近现代吟诵,还有一位先驱,那就是赵元任先生。唐文治的贡献主要在吟诵实践,立足点是文学的、国学的、教育的,赵先生的贡献主要在吟诵音乐的谱写和吟诵理论的探究,是西洋音乐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于吟诵的传承功莫大焉。赵先生早在1927年出版的《新诗歌集》的序言中就着力探讨了“吟跟唱”、“诗与歌”的不同(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引论主要观点,可参看,这里不再重复),于1961年在台湾发表《常州吟诗的乐调十七例》[70],给吟诵配上了五线谱,改变了吟诵口耳相传的单一模式,由“无乐谱的自由唱”变成了“有乐谱的自由唱”,既给吟诵插上了现代音乐翅膀,又保留了它的自由的、即兴的、弹性的节奏韵律形态。赵先生的吟诵实践亦有垂范之意义。1971年4月2日,赵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举行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活动中,用常州方言吟诵了多种文体的古诗文,明尼苏达大学刘君若教授为之录制了音带。三十年后,赵先生的吟诵理论和实践直接推动了常州吟诵的发展。可惜,解放后,在大陆教育领域吟诵很长一段时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老先生国学根基深厚,能以传统的方式吟诵,但仅限于小圈子的文人雅集,自娱自乐,击节叹赏。在极左思潮的笼罩下,吟诵被视之为明日黄花,根本不能堂皇地走上课堂。然而吟诵在邻邦日本却迅速普及并蔚成大观,吟诵诗团遍及全国各个阶层,且诗乐舞三位一体,美轮美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浪潮迭起,吟诵艺术亦得到了发掘,其魅力日益彰显。一些耆旧金针度人,积极地参与抢救、采录、传承吟诵绝学,成立了中华吟诵学会,渐呈中兴之象。综上所述,吟诵有其独特的魅力,如老树新花,生意婆娑。在多元艺术存在的今天,传统吟诵与流行歌曲、普通话朗诵可以并行不悖,然而传统吟诵的行腔使调更具韵味,更能因声而入境,让人徜徉其中,体验到古典意象世界的意境之美。一句话,传统吟诵是现代朗诵与流行歌曲之外的别一种境界。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与现代朗诵和流行歌曲相比,问津传统吟诵的人群仍然显得寥落。说白了,当下遗存的吟诵是小众文化,乃阳春白雪,但阳春白雪不接地气也会枯萎,所以吟诵不宜走士大夫式的雅化路线,当然吟诵也不是流行文化,很难歩趋大众传播的道路。吟诵教育适宜先在中小学、大学文科院系试点,以经典诵读的方式展开,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同时积极向社会文化团体渗透,让人们领略到吟诵的魅力。随着吟诵队伍的壮大,吟咏弦歌之声的不断回响,吟诵艺术便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空间。它可能不是主流文化,不能与现代朗诵与流行歌曲争一日之长,但作为古典美读,它承载着国学经典的传播,传承的方式亦别具一格,它的意义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吟诵有地域色彩,不同地域的吟诵所用方言不一样,方言吟诵与普通话推广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当前有些吟诵学家致力于方言吟诵的普通话改造,他们出版了国内第一套儿童吟诵教材《我爱吟诵》。徐健顺先生在这套书的《前言》中说:“为了便于吟诵的普及与推广,这套书全部采用了普通话吟诵。这些普通话吟诵,大部分直接来自各地的传统吟诵,只是按照普通话的声、韵、调进行了改造。”[71]吟诵的普通话改造确实能推动吟诵的普及,但我认为这种改造是不合适的,不但不能弘扬吟诵的特色,反而是对吟诵的戕害。任何一种方言吟诵都扎根在相应的文化土壤之上,现在你将它连根拔出来挪到别的土壤上,它不受伤才怪呢。
注 释
[1]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1页。
[2]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406页。
[3]任二北:《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4]任二北:《唐声诗》,第15页。
[5]赵元任:《新诗歌集·序·吟跟唱》,见《赵元任全集》第11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8页。
[6]《中国语言的声调、语调、唱读、吟诗、韵白、依声调作曲和不依声调作曲》,见《赵元任音乐论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8页。
[7]赵元任:《常州吟诗的乐调十七例》,见《赵元任音乐论文集》,第32页。
[8]赵元任:《新诗歌集·序·吟跟唱》,见《赵元任全集》第11卷,第10页。
[9]《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59~161页。
[10]这三条规律根据自己多年的吟诵体会总结,同时参考陈少松《古诗词文吟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秦德祥《绝学探微——吟诵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魏嘉瓒主编《最美读书声——苏州吟诵采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等专著的相关论述。
[1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65页。
[12]《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第166页。
[13]屠岸:《常州吟诵千秋文脉》(代序),见秦德祥《绝学探微——吟诵文集》,第4~5页。
[14]张本义:《吟诵拾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页。
[15]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
[16][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引《开元天宝遗事》,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册,第142页。
[17]叶嘉莹:《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18]赵元任先生《常州吟诗的乐调十七例》一文给吟诵谱上了五线谱,今人秦德祥出版了《吟诵音乐》一书,亦主张吟诵谱曲以便于传承,但又谓吟诵乐谱只是大致的框架,吟诵时无须受乐律的严格限制。叶先生的意见是基于文学的,而赵、秦两位先生则侧重于音乐,立场不同,是以持论相左。
[19]王恩保先生主编的《中华吟诵读本》(附光盘)采录朱福烓先生用江淮官话吟诵的作品七首。
[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页。
[21]《文心雕龙·乐府篇》,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22]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71页。
[2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340页。
[24]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295页。
[25]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493页。[26]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第364~365页。
[27]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16页。
[28]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第144页。
[29]《解闷》十二首之七,见[清]仇兆鏊:《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第1515页。
[30]卢延让《苦吟》,见《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第二十一册,第8212页。
[3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页。
[32][宋]张炎:《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5页。
[33][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宛平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6页。
[34][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第80页。
[35][明]沈德潜:《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
[36][明]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古诗》评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46页。
[37][宋]朱熹:《答何叔京》,《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79页。
[38]《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85、195页。
[39][明]刘绩:《霏雪录》,《中国历代诗话选》(二),岳麓书社,1985年,第1101页。
[40]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页。
[41]朱光潜:《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42]朱光潜:《诗论》,第195页。
[43]《周礼·仪礼·礼记》,陈戍国点校,岳麓书社,1989年,第424、429页。
[44]《周礼·仪礼·礼记》,第429页。
[45]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62页。
[46]叶嘉莹:《古典诗歌吟诵九讲·序》,第1页。
[47][清]刘大櫆:《论文偶记》,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36页。
[48]《周礼·仪礼·礼记》,第61页。
[49]《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页。
[50]《周礼·仪礼·礼记》,第428页。
[5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册,第153页。
[52]《唐文治文选》,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3~204页。
[53]《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二,第1268页。
[54][南朝梁]慧皎:《梁高僧传》卷一三《经师论》,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55][清]刘大櫆:《论文偶记》,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34~435页。
[56][清]姚鼐:《与陈硕士》,《惜抱轩尺牍》,卢坡点校,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4、96、120页。
[57][清]曾国藩:《复陈右铭太守书》,见王文濡编《续古文观止》,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79页。
[58]《曾文正公全集》第19册《家书》,岳麓书社,1995年,第418页。
[59][清]方东树:《书惜抱先生墓志后》,见《惜抱轩尺牍》,第202页。
[60][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78页。
[61]《柏枧山房文集》卷二,咸丰六年杨氏海源阁刻本。
[62]唐文治:《桐城吴挚甫先生文评手迹跋》,《茹经堂文集》三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83页。
[6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439页。
[64]此处文字录自1948年《唐蔚芝先生读文灌音片说明书》,见魏嘉瓒《最美读书声——苏州吟诵采录》,第173页。
[65]《唐蔚芝先生读文灌音片说明书》,见魏嘉瓒《最美读书声——苏州吟诵采录》,第173页。
[66]朱自清:《论朗读》,《朱自清全集》第二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67]朱自清:《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朱自清全集》第二册,第38页。
[6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63页。
[69]秦德祥:《绝学探微——吟诵文集》,第261页。
[70]此文收入《赵元任音乐论文集》(第31~42页),同时收入《赵元任全集》第11卷(第519~530页)。
[71]徐健顺、陈琴主编:《我爱吟诵》(小学中级),接力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作者简介: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文学、诗词学、音乐文艺研究。
本文原载《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2期,《文学研究文摘》2017年第1期摘录。



